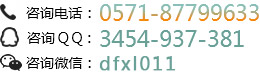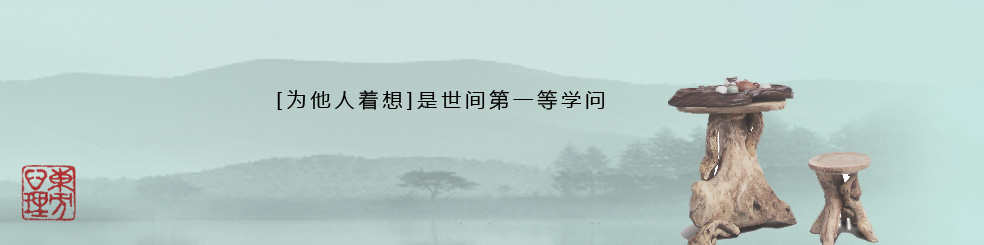
轉載自《杭州日報》2008-10-08,文/見習記者 邢人儼 圖/王毅 黃衛華

9月20日,周六。杭州慶春路某寫字樓的十一層,杭州一家心理研究機構。
從心理研究機構沙盤游戲室的落地大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見林立的高樓以及密集的車流。落地窗上裝有窗簾,平時,內層較薄的窗簾基本上是拉著的,使得室內既不會太亮,也不會太暗。這樣的光線對于來訪者來說,是一種恰當的保護。
游戲室里有兩張面對面擺放著的沙發,中間的茶幾上擺著一盒長方形的沙盤。在沙盤對面的墻上,有四個長架子,架子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小型玩具。從塑料植物到橡皮動物,從士兵模型到公主玩偶,幾乎包括了一個小孩可能玩過的各種玩具,大概有幾百種。稍不注意,都會誤以為這是玩具展覽。
游戲開始。治療師輕聲提醒我去感受一下沙盤里的沙子。我抓起一小把沙子在手里撫摩,這些取自世界各地的海沙摸起來非常的細,更確切地說,是細膩。我甚至無法分辨出它的顆粒,而覺得像是在摸一塊柔軟的綢緞。這個時候,治療師提醒我注意盒子邊緣的顏色,讓我試著撥開沙層看看下面是什么。我撥開沙層,下面是深藍色,類似于海水的顏色。突然,我覺得整個沙盤是一片海灘。
五分鐘后,我問治療師,可以去拿玩具了嗎。他點頭說,在這里你是完全自由的。
我來到玩具架子前的時候,非常不知所措。幾百種玩具已經讓人眼花繚亂了,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治療師是不是在我的后面悄悄地觀察我。我轉身偷偷看了他一眼,發現他低著頭,并沒有看我。經過一番挑選,我選擇了坐著的天使、黃禮服的公主、一對天使、一只雪白的貓頭鷹、一個滿身縫痕的古怪小女孩和一只水晶蘋果。
十多分鐘后,我開始擺放它們。這是一個既好玩又麻煩的過程,因為你必須在干凈的沙盤里按照你的想象擺。
我首先在沙盤的左下方挖出一塊圓形的藍色區域,在我看來,它像是一個湖泊。我在湖泊右邊對稱的位置擺放了坐著的天使,我覺得這樣擺畫面才是平衡的。接著我把黃禮服的公主擺在右上角,一對天使擺在湖泊前方對稱的位置,而貓頭鷹就在他們中間。然而在擺水晶蘋果和古怪小女孩時,我卻發現不知道應該把他們擺在沙盤的哪個位置。我拿著滿身縫痕的古怪小女孩在沙盤上方盤旋了好久,擺在這里覺得別扭,擺在那里也覺得別扭,舍棄不擺又覺得缺少了點什么。最后我找到了一個相對滿意的位置,把古怪小女孩擺在離我最近的右下角,把水晶蘋果擺在離我最遠的右上角。
在我擺放玩具的過程中,治療師沒有說任何話,只是靜靜地看著我擺,時不時記錄下什么,臉上甚至沒有任何表情。
當我示意他完成了沙盤之后,他說,你來介紹一下你擺的沙盤吧。坦白說,我的確不明白該如何介紹這個沙盤。
他再沒有說話,靜靜等著我開始介紹。出于無奈,我編織了一些與各個玩具有關的想象,比如天使看上去特別純潔,公主美而高貴,古怪小女孩像個精靈,水晶蘋果充滿了神秘感等等。治療師只是微笑著點頭。
“來看看這個看上去特別純潔的天使,除了純潔你覺得還有什么?”治療師問。
“生命力、溫暖、充滿光”。我說。
“那么這個特別純潔的、有生命力的、溫暖的、充滿光的天使,會使你想到怎樣的畫面?”治療師又問。
在一問一答中,我發現了很多奇怪之處。首先,治療師的問題就像是在擴句,他不斷將我說的詞語用到句子里再來向我提問。其次,他似乎永遠在提問。他沒有解釋任何象征性的問題,不評價我的回答,不做任何猜測。最奇特的一點就是,在沙盤面前,始終是我一個在說話,而治療師只是一個引導著我思路的畫外音。
隨著談話的深入,我們討論的重點落在了那個讓我舉手無措的古怪小女孩身上。治療師首先讓我來描述一下這個小女孩。我給出了“叛逆、機靈、與眾不同、古怪”幾個形容詞。治療師仍舊是微笑著點點頭,我在心里暗自為這個古怪小女孩獲得他的“認同”感到沾沾自喜。治療師接著讓我想象發生在這個古怪小女孩身上的故事。我編織了一個最符合自己感覺的故事:這個古怪小女孩推門而出,她走在路上,遇到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可能是與她一樣古怪的人,也可能是小動物,他們要一起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說完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看了看治療師,他似乎聽得津津有味。治療師又問我,看著這個小女孩,你有什么感覺。我說,我想抱抱她,然后跟著她一起去玩,我知道她一定會帶我去到一個新奇的世界。
一個小時到了。治療師最后問了一個問題“你覺得現在看這個沙盤跟剛擺出來時一樣嗎?”
這個被我忽略的問題一下讓我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也許只有親身去體驗的人才能真切感受到,之前那個毫無任何意義的沙盤最后浮現出的竟然是一種明朗而開闊的格局形態。是自己在經歷了漫長的訴說之后解釋的種種原委。盡管我并不很明確每個沙具所象征的意義或者說這個游戲的奧秘所在,但是我開始相信沙盤能夠解讀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