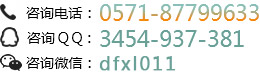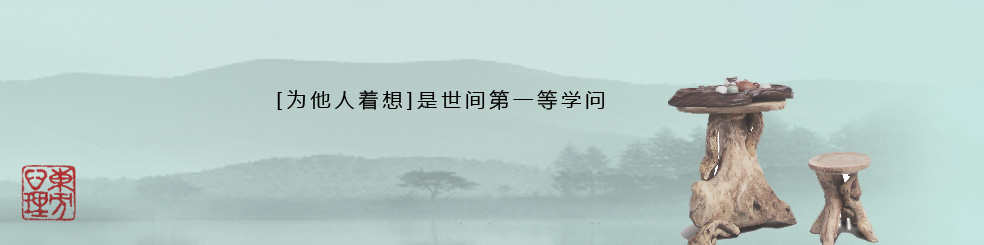
心理分析
自性化及其發展
申荷永
自性化(individuation)或自性化過程,是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的特別術語,也是其核心性的概念。你若是問榮格心理分析家們一個問題,心理分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得到的最多的答案,恐怕就是自性化了。
榮格用自性化這一概念,所要表達的是這樣一種過程:一個人最終成為他自己,成為一種整合性的,不可分割的,但又不同于他人的發展過程。安德魯·塞繆斯(Andrew Samuels)在其《榮格心理分析評論詞典》中,在比較了自性化與自性(self)、意識自我(ego)和原型(archetype)以及意識性(consciousness)和潛意識(unconscious)等概念的關系與整合意義之后說,“自性化過程是圍繞以自性為人格核心的一種整合過程。換句話說,使一個人能夠意識到他或她在哪些方面具有獨特性,同時又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男女。”[1]
從榮格1921年出版的《心理類型》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其最初對于自性化定義的表達。其基本的特征是:1,自性化過程的目的,是人格的完善與發展;2,自性化接受和包含與集體的關系,也即它不是在一種孤立狀態發生的;3,自性化包含著與社會規范的某種程度的對立,社會規范并不具有絕對的有效性。
塞繆斯曾在評介自性化的時候,揭示出其另外一個層面的意義,或人們所崇尚的自性化的陰影:“深入于內在世界及其奇異的意象,會產生趨于自戀的危險。需要考慮的另一種危險是,伴隨著自性化過程將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表現,包括反社會的行為,甚至是某種精神性的崩潰。由于移情在心理分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采用煉金術的術語,我們需要補充的是,自性化是一種逆行運動。”[2]
榮格在許多不同的背景中對自性化現象的描述,都與他個人的體驗有著密切的關系,包括他對煉金術以及煉金術者心理狀態的研究,尤其是他自己的“曼荼羅”體驗。對于榮格來說,“曼荼羅”就是自性的顯現,“曼荼羅”也包含著自性化的發展。因此,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的自性化或自性化過程,也就帶上了某種宗教性的色彩。榮格在一次回答提問時曾這樣說:“自性化是一種神性的生活,正如曼荼羅心理學清楚地表現的那樣。” [3]
國內有些學者,把榮格的自性化(individuation),望文生義地翻譯為“個體化”。這是有背榮格的本義的。榮格說,“我使用‘自性化’這一概念,是要表示這樣一種過程,在其中,一個人變得‘不可—分割’,也即成為一個獨立的不可分的整合,或‘整體’”。在榮格后期的著作中,他自己也提到區分整合與自性化時所存在的某種困難,榮格說:“我一再注意到,自性化過程容易和自我的意識化相混淆,并隨之把自我認作自性,從而使問題更加復雜。這樣自性化就僅僅是自我中心和自發的性欲(auto-eroticism,可參考“自戀”,narcissism)……自性化并不與世隔絕,而是聚世界于己身。”于是,自性化的思想是在強調和突出某種獨特性,而不是強調集體性的考慮和責任。但是,自性化又確實意味著更好并且更加全面地實現集體特性。或者用榮格自己的話說,“自性化的目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為自性剝去人格面具的虛偽外表;另一方面,消除原始意象的暗示性影響。”[1]
從臨床心理分析或方法論的角度來說,自性化并不是由分析家所引起的,分析家不能將自性化給予病人,也不能要求病人自性化的出現。一位好的心理分析家所能做的,僅僅是創造一種能夠促進自性化過程的環境,并且以其所能表現的耐心和同情在旁守望。在榮格分析心理學的理論中,自性化被看做是一種源自無意識自然發生的過程。作為心理分析家,并不能任意干涉,尤其是不能用自己的意識來妄加干涉,不管是促進還是阻礙。
然而,整個心理分析的過程,包括以一種開放性的態度來對待病人潛意識的表現,包括認識與理解夢和原型意象的象征性意義,以及認識與理解自己的陰影,溝通自己的阿尼瑪和阿尼姆斯等等,都是與自性化過程密切相關的實際工作。在這種意義上,心理分析家仍然是積極與主動的。
(摘自《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申荷永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一版。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