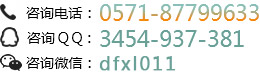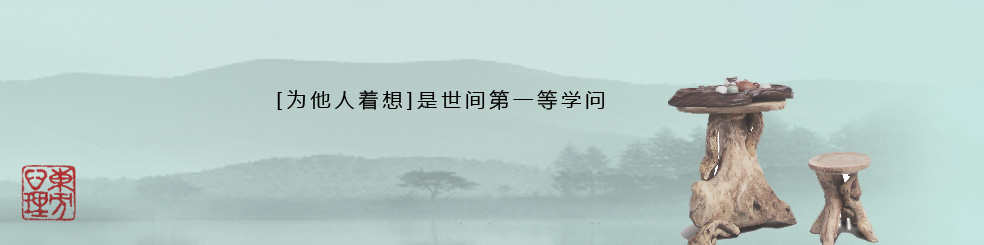
心理分析
集體無意識(shí) 與 原型
申荷永
集體無意識(shí)(collective unconscious)既是對(duì)弗洛伊德個(gè)體潛意識(shí)(personal unconscious)的發(fā)展,也是榮格的一種創(chuàng)造。榮格用它來表示人類心靈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遺傳。或者說,集體無意識(shí)中包含著人類進(jìn)化過程中整個(gè)精神性的遺傳,注入在我們每個(gè)人的內(nèi)心深處。
榮格自己在給集體無意識(shí)做定義的時(shí)候,曾經(jīng)這樣說:“集體無意識(shí)是精神的一部分,它與個(gè)人無意識(shí)截然不同,因?yàn)樗拇嬖诓幌窈笳吣菢涌梢詺w結(jié)為個(gè)人的經(jīng)驗(yàn),因此不能為個(gè)人所獲得。構(gòu)成個(gè)人無意識(shí)的主要是一些我們?cè)?jīng)意識(shí)到,但以后由于遺忘或壓抑而從意識(shí)中消失的內(nèi)容;集體無意識(shí)的內(nèi)容從來就沒有出現(xiàn)在意識(shí)之中,因此也就從未為個(gè)人所獲得過,它們的存在完全得自于遺傳。個(gè)人無意識(shí)主要是由各種情結(jié)構(gòu)成的,集體無意識(shí)的內(nèi)容則主要是原型。”[2]
榮格在其自傳中說,他關(guān)于集體無意識(shí)的思想,得自于1909年與弗洛伊德一起訪美歸來的途中所做的一個(gè)夢。榮格曾這樣陳述他的夢:
(在夢中)我的身處在一所我不認(rèn)識(shí)的兩層樓的屋子里。但它是“我的房子”。我發(fā)現(xiàn)自己是在樓上,有點(diǎn)像是客廳的感覺,做工精致的老式家具,以及墻上懸掛著一些古老的珍貴名畫。我奇怪這陌生的房屋怎么會(huì)是我的家。不過我想,“還不錯(cuò)。”于是我更想知道一樓是怎樣的,便沿著樓梯走到了樓下。在這里,一切東西都顯得更加古老,我意識(shí)到房子的這一部分大概可以追溯到15或16世紀(jì)。家具陳設(shè)似乎是中世紀(jì)式的,地面鋪的是紅磚。這里的光線不足,顯得陰暗一些。我從一個(gè)房間走到另一房間,心里想道,“唔,我實(shí)在得探究一下這整座屋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門前,用力打開了它。在門的那邊,我發(fā)現(xiàn)了一道通向地下室的石砌梯級(jí)。于是我就走了下去,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自己處在一個(gè)有拱頂?shù)拿利惖姆块g之內(nèi),而這房間則顯得極為古老。在仔細(xì)察看四周時(shí),我發(fā)現(xiàn)在普通的大石塊上砌有一層層的磚,而且在灰漿里也有磚頭的碎塊。我一看到這個(gè),便知道這面墻壁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shí)代。于是我的興趣便高漲起來。我更加仔細(xì)地觀察著地板,發(fā)現(xiàn)它是用石片鋪成的,在這些石片內(nèi)我發(fā)現(xiàn)有一個(gè)環(huán)。當(dāng)我拉動(dòng)這個(gè)環(huán)的時(shí)候,石片便抬了起來,我再次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級(jí),通往地下更深處。我沿著這些石級(jí)走了下去,最后便走進(jìn)了一個(gè)在巖石里鑿成的低矮的洞穴。石洞的地面上蓋有一層厚厚的灰土,灰土中散布著一些骨頭和陶片,像是一種原始文化的遺物似的。我看到兩個(gè)人的頭蓋骨,顯然也是很古老的,都有些要裂開了。這時(shí),我便醒了。[1]
在往返美國訪問的途中,榮格與弗洛伊德曾有幾次相互分析各自的夢。當(dāng)榮格向弗洛伊德講述這個(gè)夢的時(shí)候,弗洛伊德尤其關(guān)注那兩個(gè)死人的頭蓋骨,以及透過這夢中的頭蓋骨,榮格是否具有某種希望某人永遠(yuǎn)死去的聯(lián)想。但對(duì)于榮格來說,這個(gè)夢中的房子即是一種精神大廈的象征:比如,樓上的客體,顯然就是意識(shí)或意識(shí)層面,而陰暗的樓下,可以說是無意識(shí)的第一層。當(dāng)榮格自己分析這個(gè)夢的時(shí)候,他激動(dòng)地說:“(在夢中)我越深入,景象便變得越生疏和越黑暗。在那個(gè)洞穴里,我發(fā)現(xiàn)的是一種原始文化的殘存物,亦即我身上的原始人的那個(gè)世界,這個(gè)世界是意識(shí)所幾乎無法接近和照亮的。人的原始性精神近乎動(dòng)物靈魂的生命,恰如史前時(shí)代的洞穴在為人所占有之前通常是由野獸所占據(jù)的一樣。”[2] 于是,榮格有了這樣一個(gè)夢,也就有了他的集體無意識(shí)的原型,當(dāng)他的這一思想不斷地被其臨床實(shí)踐所證實(shí)的時(shí)候,他也就逐漸地形成了關(guān)于集體無意識(shí)的理論。
原型
榮格的原型(archetype)概念與其集體無意識(shí)十分密切。正如他所曾明確表達(dá)的那樣,個(gè)人潛意識(shí)主要是由各種情結(jié)構(gòu)成的,而集體無意識(shí)的內(nèi)容則主要是原型。榮格說,“原型是人類原始經(jīng)驗(yàn)的集結(jié),它們(榮格往往把原型作為復(fù)數(shù))像命運(yùn)一樣伴隨著我們每一個(gè)人,其影響可以在我們每個(gè)人的生活中被感覺到。”[3]
榮格認(rèn)為,集體無意識(shí)是通過某種形式的繼承或進(jìn)化而來,是由原型這種先存的形式所構(gòu)成。原型賦予某些心理內(nèi)容以其獨(dú)特的形式。同時(shí),榮格還提出,主要是由原型所構(gòu)成的集體無意識(shí),具有一種與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個(gè)人皆符合的大體相似的內(nèi)容和行為方式。由于集體無意識(shí)具有這樣一種普遍的表現(xiàn)方式,因此它就組成了一種超個(gè)人的心理基礎(chǔ),普遍地存在于我們每個(gè)人身上,并且會(huì)在意識(shí)以及無意識(shí)的層次上,影響著我們每個(gè)人的心理與行為。在這種原型心理學(xué)的意義上,榮格認(rèn)為,歷史中所有重要的觀念,不管是宗教的,還是科學(xué)的、哲學(xué)的或倫理的觀念,都必然能夠回溯到一種或幾種原型。這些觀念的現(xiàn)代形式,只是其原型觀念的不同表現(xiàn),是人們有意識(shí)或無意識(shí)地把原型觀念應(yīng)用到了生活現(xiàn)實(shí)的結(jié)果。[4]
榮格所使用的原型概念,就其西方思想的起源來說,在柏拉圖所論述的“形式”中,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了這種原型觀念的痕跡。列維—布留爾在其《原始思維》中使用“集體表象”時(shí),更是接近了榮格所描述的作為集體無意識(shí)的心理原型。根據(jù)列維—布留爾的描述,“集體表象”在某一集體(該集體可以是一種文化,或一個(gè)民族)中世代相傳和繼承,并且在該集體的每個(gè)成員身上都會(huì)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時(shí),根據(jù)不同的情況或作用方式,“集體表象”還能夠引起該集體中每個(gè)成員對(duì)有關(guān)的表象和象征物產(chǎn)生尊敬、恐懼、崇拜等感情。[1] 實(shí)際上,斯賓格勒在其《西方的沒落》中,也提出并使用了類似的觀念。他用其生命圖像,向歷史和文化注入了一種心理化的自我和人格的色彩,并且認(rèn)為,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dú)特的觀念,有其生活的愿望和情感,并且也都會(huì)有其象征性的表現(xiàn)和表現(xiàn)方式。[2] 某一文化中獨(dú)特觀念的象征性圖象,便具有一種心理原型的意義和作用,因?yàn)檫@種圖象在該文化的歷史中反復(fù)出現(xiàn),對(duì)該文化中的所有成員都會(huì)產(chǎn)生思想與觀念上的影響。
記得在美國舊金山的一次主題為榮格的原型專業(yè)研討會(huì)上,許多參加者,盡管其本身都是資深的心理分析家,但提問與討論之中,仍然表現(xiàn)出對(duì)原型帶有許多疑慮。當(dāng)時(shí)的我想到了老子的智慧。既然榮格試圖通過原型這一概念來描述某種人類心靈深處的事實(shí),那么,對(duì)于這種存在的事實(shí),老子也會(huì)有所洞察的。
老子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fù)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jì)。”[3]
講課的是一位備受尊重的資深心理分析家,在大家熱烈討論而未能獲得對(duì)原型理解的時(shí)候,聽到老子的這些闡述,她本人以及所有參與研討會(huì)的學(xué)生,都表現(xiàn)出了特別的欣喜與感激。榮格曾一再強(qiáng)調(diào),原型從其本質(zhì)上說完全屬于無意識(shí)的存在,我們是無從認(rèn)識(shí)它本身的;但是原型卻可以通過原型意象來表現(xiàn)其無意識(shí)的意義。盡管“道可道非常道。”但是“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說,“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4]
[2] 榮格:“集體無意識(shí)的概念”,馮川編譯:《榮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頁。
[1] 關(guān)于榮格的這個(gè)夢,可參見榮格:《回憶?夢?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158—160頁。或劉國彬等的中譯本270—272頁。
[2] 同上。
[3] 榮格:《原型與集體無意識(shí)》,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Princeton 1977,P.30.
[4] 榮格:《心靈的結(jié)構(gòu)》,The Structure of the Psych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8. Princeton 1977 P.342.
[1] 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丁由譯,商務(wù)印書館1986。
[2] 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導(dǎo)言》,齊世榮等譯,商務(wù)印書館1995。
[3] 《老子》第十四章。
杭州東方心理分析研究所 www.weixiuqun.com 備案號(hào):浙ICP備13001446號(hào)-1
電話:0571-87799633 地址:杭州市蕭山區(qū)山陰路590號(hào)金帝高新科技廣場3號(hào)樓西單元801室
優(yōu)化支持:誠速寶
首頁
| 關(guān)于東方
| 核心服務(wù)
| 常見心理問題
| 機(jī)構(gòu)動(dòng)態(tài)
| 專業(yè)園地
| 咨詢指南
| 下載中心
| 聯(lián)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