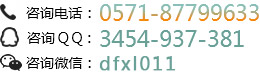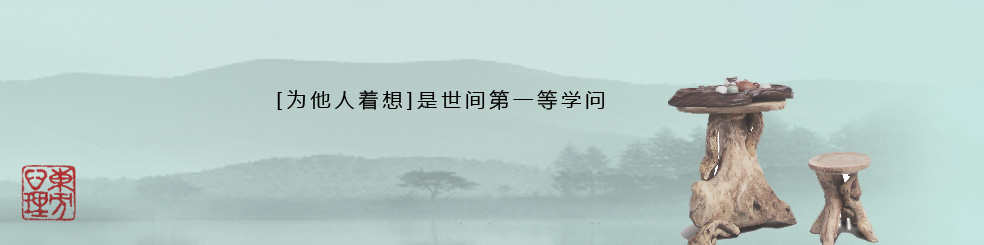
心理分析
榮格是誰?
申荷永
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的時候,世界籠罩在戰(zhàn)爭的硝煙與陰影之中,榮格也在他的無意識領(lǐng)域探索著。在以后的20多年中,世界格局以及心理學(xué)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反法西斯的戰(zhàn)爭最終取得了勝利,戰(zhàn)爭考驗了心理學(xué)的應(yīng)用,也促進了心理學(xué)的發(fā)展。由于恢復(fù)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需要,精神分析更加受到重視;人本主義心理學(xué)和認知心理學(xué)都呈現(xiàn)出其潛在的意義,榮格與其分析心理學(xué)也獲得了長足發(fā)展。
卡爾·榮格印象
若是從照片上來看,年輕時的榮格與老年的榮格給人截然不同的印象。一是強硬與果敢氣質(zhì)的表現(xiàn),一是神秘而富有智慧的感覺。實際上,強硬、神秘與智慧,這都是人們對于榮格的基本印象。
(一)石頭中的情結(jié)
榮格有著深深的“石頭情結(jié)”,他的心理分析也與“石頭”有著不解的淵源。在其自傳《回憶·夢·思考》中,曾有這樣一段對自己童年經(jīng)驗的描述:“‘我坐在下面的石頭上,’但是這石頭也可以說‘我’并且想:‘我躺在這斜坡上,他坐在我上面。’于是就產(chǎn)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我是坐在石頭上的那個人呢?還是被那個人坐著的石頭?’這樣的想法總是困惑著我,于是我會站起來,想分清楚到底誰是誰。”[1]
榮格回憶說,這個問題長久而得不到答案,一種奇怪的思慮一直伴隨著自己。“但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這塊石頭和我有著某種神秘的關(guān)系,我可以在上面一坐好幾個小時,被它所提出的謎一樣的問題逗引得暈頭轉(zhuǎn)向。”
那時他還只是一個七八歲的孩子。30年過后,榮格已經(jīng)成家立業(yè),功成名就。他站在那道斜坡上,再看童年時曾坐著幻想的石頭,他說“突然我又變成那個曾經(jīng)點一堆意義神秘的火、并且坐在石頭上苦思靈想究竟石頭是我,還是我是石頭的孩子了。”[2]
就是這么一塊普通的石頭,使榮格獲得了深遠的思想。后來,榮格知道這是他與“道”的緣分,一種自然的心靈的感應(yīng)和溝通。于是,像許多西方的學(xué)者一樣,榮格對 “蝴蝶道者”的莊子十分神往。坐在石頭上的榮格,幻想著“自我”與“石頭”的互換,極為類似莊周與蝴蝶的“物化”體驗。
榮格深信,這石頭與他有著某種神秘的關(guān)聯(lián),甚至把石頭作為他“第二人格”的象征。榮格在其自傳中說:“每當(他)想到(他)是石頭的時候,便會產(chǎn)生一種舒適感……”“石頭安定而實在,沉默不語,千萬年來保持著如此的稟性。”榮格曾深有感觸地說:“(他)所具有的另外一種存在(其第二人格),就是那永恒而不朽的石頭。” 于是,榮格與“石頭”有著不解的淵源。他曾經(jīng)說這種關(guān)聯(lián)是一種“血緣的關(guān)系”,并且認為這種關(guān)系是“存在的無盡神秘,心靈的具體表現(xiàn)。”[1]
“石頭情結(jié)”伴隨著榮格的一生。他用石頭建筑了他的波林根塔樓,他在隱居中感悟智慧。而他留在波林根的石刻,就像波林根一樣著名,尤其是那“三面刻石”,幾乎就是榮格心理分析的象征。
在石刻的正面,面向塔樓的東面,榮格自己在石頭的紋路中“看到”了一個“圓圈”,像是一只大眼睛在看著他。于是他就刻了這么一個圓圈,并且在中間還刻了一個小矮人,包含著“你在別人眼睛的瞳孔里所看到的你”的意思。這“小矮人”身穿鐘形斗篷,手持一盞燈,儼然像一位指路人。榮格用拉丁文刻了這么一段話:
“時光是個孩子…… 像孩子那樣在玩耍……玩著棋盤游戲……孩子的王國與天下。這就是泰雷斯富魯斯(Telesphoros)[1],他在這宇宙的黑暗處徜徉,像透過夜空的星星那樣閃閃發(fā)光。他指引著通往太陽和夢國之門的道路。”
在石刻的第三面,也就是朝向湖的那一面,榮格說是他讓石頭自己“說話”的,石頭“說”了什么,他就刻上什么:“我是一個孤兒,孤獨一人。然而我浪跡著天涯。我是一個人,但卻又與自己相反。我同時是青年人和老人。我不知有父也不知有母,因為我曾像魚一樣在深水中被撈起,或像是一塊從天而降的白色的石頭。我游蕩在樹林山間,但又隱藏在人們的心靈深處。對每一個人來說,我也是必死的凡人,但我又不受生命輪回的影響。”
榮格說,“這石頭佇立在塔樓的外面,像是對這塔樓的注解。它也正是那居住者的心聲,只是尚不為他人所理解。”榮格也曾問那些好奇的人:“你知道我想在這石頭的背面刻什么嗎?”石頭中仍然包含著許多秘密。榮格說這石頭使他想起梅林,想起梅林從森林深處發(fā)出的呼喊。于是,“梅林的喊叫聲”(Le cri de Merlin)[2] 就是那未刻上去的文字。人們?nèi)匀豢梢月牭剿暮敖新暎侨藗儏s無法理解或解釋這叫喊聲。
這是榮格的石頭情結(jié),也是他要在其心理學(xué)中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其分析心理學(xué)所包含的神秘色彩。
(二)神秘中的探索
記得在一次關(guān)于榮格心理學(xué)的講座中,主持人想著讓大家談一下各自對榮格的印像,類似于自由聯(lián)想或詞語聯(lián)想的練習(xí)。參加者80余人,最集中的回答便是“神秘”。終日坐在石頭上幻想的孩子,是顯得神秘的,或至少伴隨著某種神秘的氣氛。而這種終日的神秘向往,導(dǎo)致了榮格童年的另一個神秘事件的發(fā)生。
榮格在其自傳中記述到:“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時刻,它像一閃即逝的電光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榮格在其上學(xué)用的尺子上,刻了一個小矮人:“大約兩英寸高,穿禮服,戴著高帽子,腳登一雙亮閃閃的黑輪靴子。”榮格用墨水把它染成黑色,然后從尺子上鋸下來,放在鉛筆盒里。同時,榮格還在鉛筆盒里給這小矮人做了一張小床,用一點兒羊毛給它做了件大衣。同時,榮格去萊茵河邊給這小矮人找來一塊光滑的長方形的黑石頭,也放進了鉛筆盒。
榮格說這一切都做得極為神秘。他悄悄地把鉛筆盒拿到房頂?shù)拈w樓,藏在一根大梁上,他為此感到極大的滿足和快慰。“我經(jīng)常每隔幾個星期,躲開人們的注視、溜上閣樓,爬上大梁,打開鉛筆盒,看看我的小人和他的石頭,每次我還要在盒子里放一個小紙卷,上面是我在學(xué)校寫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語言。”
榮格說,“心中藏有秘密,對我的性格的形成影響巨大。我認為這是我童年時代的本質(zhì)特征。”而這種藏有秘密的孩子的神秘氣氛,也就不僅僅是榮格童年時代的本質(zhì)特征,也是榮格成長與發(fā)展的主要特點。
從他讀大學(xué)開始,盡管讀的是醫(yī)學(xué),榮格對于心靈的神秘感再次浮現(xiàn)。即使是閱讀一些有關(guān)心靈感應(yīng)或超心理學(xué)的書籍與資料,在當時絕大部分的學(xué)者眼中那純屬無稽之談,榮格卻總是傾向于接受與相信其真實性。榮格在其自傳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說:“對我自己來說,我覺得這種種可能性是極為有趣和極為吸引人的。它們給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個新天地;世界具有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說,夢有可能與鬼魂有點什么關(guān)系嗎?”[1]
在榮格的自傳《回憶·夢·思考》中,記錄了這樣兩個事件。其一,在1898年暑假的一天,榮格正坐在房間里學(xué)習(xí)功課。隔壁飯廳的門敞開著,飯廳里有一張胡桃木的餐桌,是榮格祖母的嫁妝,已有七十多年了。榮格的母親坐在里面織毛線。突然間,砰地一聲作響。榮格跳起來快步?jīng)_進房間,只見他母親目瞪口呆地坐在扶手椅里,毛線團從她手里落到了地上,直盯著那張桌子。響聲正是那胡桃木餐桌發(fā)出的,桌面上顯出了一道長長的裂縫。榮格的媽媽深沉地說:“這一定是意味著什么。”
榮格的神秘感從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他母親。他曾回憶到,在他小的時候,一到夜里,母親就顯得古怪和神秘。而這古怪與神秘的氣氛,也帶給榮格很多古怪而神秘的夢。
在胡桃木餐桌裂開的兩周后,榮格從學(xué)校回到家里,發(fā)現(xiàn)全家人正處在激動不安的狀態(tài),原來又發(fā)生了同樣的驚響,但不再是胡桃木餐桌的裂開,而是放在餐具柜里的一把餐刀,斷裂成三節(jié)。在那以后,榮格開始參加他親戚家里舉行的“降神會”,幾個星期以后,他聽說幾個親戚在搞桌子轉(zhuǎn)動的事:他們當中有一個降神者,一個15歲或16歲的年輕姑娘。這幾個人一直想讓他見見這個降神者,據(jù)說這個姑娘能使人進入夢游狀態(tài)并能招魂。當他聽到這個消息,便立刻想到了在他屋里的那種古怪的現(xiàn)象,于是他便猜想,它們可能以某種方式與這位降神者有聯(lián)系。于是,他便開始列席“降神會”。
就在這“降神會”里,榮格發(fā)現(xiàn)了他表妹海琳(Helene Preiswerk)的特異能力,并開始以她為研究對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論所謂神秘現(xiàn)象的心理學(xué)和病理學(xué):一種精神病學(xué)研究》(1902)。而他從巴塞爾大學(xué)畢業(yè)之后,提交給布勒霍爾茲利精神病院的就職論文,仍然是關(guān)于《超自然現(xiàn)象》的研究。這種對“超心理學(xué)”(parapsychology)和“特異心靈現(xiàn)象”的研究興趣,一直伴隨著榮格的整個一生。榮格在面對無意識的探索過程中“遇到”““斐樂蒙””(Philemon),在”“斐樂蒙””的啟發(fā)下撰寫《向死者的七次布道》,都充滿著這種神秘的色彩。就是到了晚年,榮格仍然對“飛碟現(xiàn)象”倍感興趣。
但是,這種“神秘”或“神秘的色彩”,在榮格的生涯中得到了積極與有效的發(fā)揮,盡管保留著其消極和迷信的成分。當這種神秘促進探索的時候,總是積極的,那也正是探索未知的科學(xué)精神;當這種神秘融入智慧的時候,更成為一種精神的升華。
(三)隱居中的智慧
榮格曾自稱是一個孤獨者,尤其是尼采意義上的孤獨者。他也曾在晚年隱居他的波林根,自己在蘇黎世的郊外所建造的塔樓。隱居是顯得神秘的,但隱居者與孤獨者也往往是智者。隱居與孤獨培育著智慧。
榮格在1902年買下了位于蘇黎世湖盡頭的波林根的一片土地。那里本來是教堂的地產(chǎn),早先屬于圣嘉爾修道院。1923年榮格的母親去世后,他著手建造塔樓的最初結(jié)構(gòu),后來有幾次擴建,歷時12年完成了波林根的塔樓。1947年榮格72歲時,正式退隱波林根。
在今天看來,波林根是湖光山色且?guī)в刑飯@色彩十分優(yōu)美的地方,但是,在榮格隱居那里的時候,實際上直到現(xiàn)在,塔樓里沒有任何通電的設(shè)備,沒有電燈電話,沒有空調(diào)與冰箱。榮格自己曾這樣來描述他在那里的生活:
“這里沒有電力設(shè)施,天冷的時候我靠向火爐取暖。傍晚時分,我燃起油燈。這里沒有自來水,我從井中打水;我劈柴用來燒飯。這些簡單的工作使人變得簡單;但是變得簡單又是何等的艱難!”[1]
簡單接近自然,簡單能夠使人單純。榮格說,“在波林根,我處身于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之中,我極為深切地恢復(fù)了本來面目。”他在那里有自己的一間“沉思室”,退隱中更為隱秘的地方。榮格說每當他進入那房間,就會感到一種輕松與自然。“思緒不斷地涌現(xiàn),回蕩著多少個世紀的往事,也預(yù)現(xiàn)著那遙遠的未來。在這里,那創(chuàng)造的痛苦得以緩解,創(chuàng)造與游戲密切地結(jié)合在了一起。”[2] 于是,榮格感觸地說,“住在波林根的這座塔樓里,一個人便仿佛同時生活在許多世紀似的。”
在《回憶·夢·思考》中,榮格是這樣描述他的波林根以及他在波林根的感受的:
我時常覺得我自己也伸展向那無際的曠野以及周圍一切存在的內(nèi)部。我覺得我是生活在每一棵樹中,每一朵浪花的耀動之間,生活于云霧與動物的穿梭,以及季節(jié)的變化之中。這塔中的一切已經(jīng)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注入了其自己的特色,而每一特色也都與我息息相關(guān)。在這里,任何一樣?xùn)|西都有它自己以及和我的歷史,這里是心靈特有世界的無限的王國。
在漢娜撰寫的榮格傳記《榮格的生活與工作》中,她把1945—1952稱為榮格的“豐收”季節(jié)。榮格曾于1944年生了一場重病,嚴重的心臟血栓,多虧一位H醫(yī)生,才使得他死里逃生。此后榮格修養(yǎng)了很長一段時間,接著,漢娜寫道:“榮格便進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時期。在此期間,他最重要的幾部書寫成了。”[3] 而榮格自己也曾十分明確地回憶說:
經(jīng)過那場疾病之后,一個豐富的工作階段開始了。我的許多重要的著作都是那時候完成的。我所獲得的靈感,或者是對于所有問題的本質(zhì)性洞察,使我獲得勇氣來表達新的思想與理論。我不再試圖闡述自己的意見,而是讓自己沉浸于新的思想之中。于是,問題一個接一個自行向我展現(xiàn)并且獲得其表達的形式。[4]
在榮格自傳《回憶·夢·思考》的最后一頁,榮格援引老子的話:“眾人皆清,惟我獨懵。”作為其自傳的最后總結(jié)。榮格說,老子所表達的正是他在老年所感受到的。榮格稱老子就是一個完美的象征,他具有超越的智慧,可以看到以及真切地體驗到價值與無價值。受老子的影響,榮格在其晚年渴望著回歸其本來的存在,回歸那永恒的未知的意義。榮格說:“智慧老人的原型所洞察的是永恒的真理……我對于我自己越是感到不確定,越是有一種內(nèi)在生發(fā)的,與所有的存在均有聯(lián)系的感覺。事實上,似乎那長期以來使我脫離于世界的疏離感,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我內(nèi)在的世界,同時展現(xiàn)給我一種意外而新穎的我自己。”[5]
于是,孤獨與隱居,體現(xiàn)為榮格的智慧。榮格去世前曾有這樣兩個夢境。一是關(guān)于波林根的:在夢中,“他看見了‘另一個波林根’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下,一個聲音對他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完工了,可以準備住人了。”另外一個夢,也是漢娜記在其《榮格的生活與工作》中的,就在榮格去世前的某個晚上,榮格在夢中看見一塊大的圓石頭,上面刻著:“這是你的完整性和同一性的標記。”[1] 于是,石頭、神秘與智慧結(jié)合在了一起。這是我們所看到的榮格,也是榮格留下來的印象。
[1] 榮格:《回憶?夢?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20頁。
[2] 同上。
[1] 榮格:《回憶?夢?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42頁,第68頁。
[1] 泰雷斯富魯斯(Telesphoros):傳說中醫(y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或Asklepios)的兒子,健康女神海吉爾(Hygieia)和治愈女神潘娜希(Panacea)的兄弟。
[2] 梅林:傳說是阿瑟王時代的詩人和巫師,據(jù)說曾被女巫關(guān)入巖石中,后被魔法困在荊棘叢中,從此便一直深睡,但有時人們卻可以聽見他的叫喊。
榮格對“梅林”的注解:梅林代表了中世紀的無意識想創(chuàng)造一個與巴斯法爾(Parsifal)對等的人物的意圖。巴斯法爾是個基督徒中的英雄,而梅林這個魔鬼和一個純潔的處女所生的兒子則是前者的陰暗的兄弟。在12世紀這個傳說產(chǎn)生的時候,仍然沒有存在著什么可以據(jù)之以了解他那固有的含義的任何前提。因而他的故事便以流放作結(jié),因而也就有了“梅林的喊叫聲”一說,而這喊叫聲在他死后仍然從森林里傳出來。沒有人能夠理解的這種喊叫聲意味著他仍然以無法贖救的形式而活著。他的故事仍然沒有結(jié)束,他仍然在到處走動著。可以這樣說,梅林的秘密由煉丹術(shù)而流傳下來了,而且主要是通過墨丘利烏斯(Mercurius)這個人物才流傳下來的。因此,梅林這個人物是在我那無意識心理學(xué)里被再次提及,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個謎,無法理解。這是因為大多數(shù)人覺得,要與無意識密切地一起生活可太難做到了。我反復(fù)多次才懂得了,要做到這樣對于人們來說是多么的難。
[1] 榮格:《回憶?夢?思考》,劉國彬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頁。
[1] 榮格:《回憶?夢?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225—226頁。
[2] 同上。
[3] 芭芭拉·漢娜:《榮格的生活與工作》,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頁。
[4] 榮格:《回憶?夢?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297頁。
[5] 榮格:《回憶?夢?思考》,英文版,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第359頁。
[1] 芭芭拉·漢娜:《榮格的生活與工作》,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53頁。
杭州東方心理分析研究所 www.weixiuqun.com 備案號:浙ICP備13001446號-1
電話:0571-87799633 地址:杭州市蕭山區(qū)山陰路590號金帝高新科技廣場3號樓西單元801室
優(yōu)化支持:誠速寶